我们村的最后一个地主
冯积岐
1
头发白了,胡须白了,眉毛白了,身材也不端直了,消瘦而爽朗的脸庞上总是挂着笑,那笑容仿佛版画家用刻刀固定在木板上一样,线条明朗得如同春雨洗濯之后那瓦蓝瓦蓝的天空。他,就是我的祖父冯巩德。祖父的笑跟婴儿的笑差不多:单纯、天真、自然,缺少打扮,缺少内涵。祖父的高寿似乎就扎根于他那无拘无束的笑容里。他的生命和他的笑容一样顽强一样精神。
祖父活得很不容易,但他活下来了,活到了我们村里的最后——最后一个地主。
祖父将我们村里在一九四九年的土地改革中戴上“帽子”的十六名地主分子和在一九六四年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补定的十四名地主分子奉陪到底了,陪进了黄土之中。祖父还活着。
祖父将我们南堡乡在一九四九年的土地改革中戴上“帽子”的一百六十八名地主分子和在一九六四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补定的一百四十四名地主分子奉陪到底了,陪进了黄土之中。祖父还活着。
展开全文
就在我着手写这篇小说前,打电话问我们凤山县的常务副县长史晓辉,凤山县还有多少地主分子健在?史晓辉告诉我,凤山县的六千二百七十九名地主分子,除过我的祖父以外,全都过世了。
也许,祖父是我们西水市是我们陕西省的最后一个地主分子。其实,是不是,已经没有必要去考究了。祖父的活着不是石破天惊的事情,也不是一个奇迹,但绝对是一个话题,是一个标志,是一个证据,是一段活生生的历史见证:祖父把历史中的某个内容苟延残喘地向前扯动着……
祖父真能活!医生在祖父的身体检查报告上写道:冯巩德的各个脏器尚好。祖父的神志清楚,记忆不差,耳朵不聋,目光也能准确无误地将人或事物逮住。2001年农历三月十四日,祖父不屈不挠地迎来了他的九十二岁生日。
当晨光尚在村子外面那棵高大挺拔的古槐树的枝叶间聒噪之时,祖父起来了。他下了炕,趿上鞋,走出去,打开了院门。父亲听见了院门的响动声,随之出了房间,他一看,祖父在院子里走动,搬出来祖父的躺椅,放在了房檐台上。父亲要将祖父扶上躺椅,祖父不叫父亲扶。父亲给祖父说,今天,谁也不用你招呼,你就安安生生地在躺椅上躺着吧。祖父说:大家给我来祝寿,我咋能躺着不动呢?父亲说:招呼人的事我安排好了,不用你劳累。祖父说:村长乡长来,我也不管,我只招呼你广顺爸一个。松陵村的冯姓人家中只剩下我们两个老汉是大寿了。父亲说:那好吧,让他陪你说话。在祖父这一房系,祖父排行老三。冯广顺和祖父不是一个房系的,在他们那一房,冯广顺排行老七。按辈分,我们这一代该叫冯广顺七爷了。可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冯广顺不认祖父为三哥,我们就不敢叫冯广顺七爷了,因为他是村里的干部。
祖父在院子里走动了一会儿,进了房间。他右手端着一个四方形的铁盒子,左手拿一杆烟锅,又出来了。祖父将盛烟叶的盒子和烟锅放在躺椅跟前的茶几上,坐进了躺椅。祖父的一双手搭在膝盖上,面对着东方,一动不动的,仿佛将整个身心浸泡在清水一样滋润鲜活的晨光里,沐浴着天籁。这时候的祖父如同一棵百年老树,好像一段深沉的箴言,仿佛一个守候在生命前沿的“兵马俑”;他是一副安详、平静、坦然,很超脱的样子。祖父默坐了一刻,拿起烟锅,开始向烟锅里装烟。祖父不吃纸烟,再好的纸烟也不吃。他的炕头上总是放着牌子很亮的纸烟,那是用来招待人的。每逢广顺到家里来,祖父将纸烟抽出来递给广顺,自己拿起烟锅在烟盒里挖。广顺接过去纸烟,没有即刻点火,他用三根枯瘦的指头将纸烟撮起来,左端详,右端详,问祖父:这一支烟得多少钱?
祖父说:你管他多少钱,吃吧,反正是儿子买的。广顺说:你说说,让我开开眼界。祖父说:一支大概一块半钱吧。广顺一听,长长地“咦”了一声:吃一支烟,要二斤麦子钱。广顺点上烟,贪馋地吸几口说:三哥呀,你那土地主的样子几十年不变。祖父笑模笑样地扫了广顺一眼,笑模笑样地给烟锅里装烟。祖父的烟锅有一尺多长,黄铜烟锅和黄铜烟锅嘴子散发着年代久远的气息,陪伴了祖父半个世纪的烟锅被一双手磨搓得如同灯光一样闪亮光滑。祖父吃了一锅烟。右手攥着烟锅杆子在躺椅跟前的茶几腿上磕着,磕着……
2
当时,祖父只将烟锅磕了两下,烟灰还没有磕尽。广顺一开口,祖父就不再磕了,他的右手紧攥住烟锅杆子,用烟锅朝广顺一指,粗声喝问:你说!你去来没有?祖父端坐在紧靠住方桌的红漆椅子上。方桌上堆放着亲戚们用麦面做的“寿桃”。祖父用冷峻威严的目光将广顺压住,左手按在方桌上,仿佛要将满腔的愤怒狠狠地按进木纹里去。广顺站在祖父跟前,低垂着脑袋,嘴里胡支吾。
这时候,祖母迈着轻盈的步子走进了木面楼房的客厅,她一看,祖父脸色铁青,密而黑的眉毛似乎竖起来了,祖父像审贼似的正在审问广顺。祖母说:看你!今天过寿哩,发啥脾气?祖父用眼角的余光刺了祖母一眼没有搭理她,依然喝问广顺:说话呀,到底去来没有?广顺低眉垂眼,一只脚动了动,还是没有正面回答祖父。祖母说:客人还没有走尽哩,就高喉咙大嗓子地吆喝,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咱向来对长工这么恶。祖父将烟锅在方桌上很响地一磕,飞快地弹了祖母一眼,厉声说:走开!这不是你多嘴的地方。祖母一看,祖父的怒气像汗水一样满脸都是,她闭上了嘴,轻手轻脚地走出了客厅。
片刻,祖父像石崖一样陡峭的语气舒缓了些:广顺,你得是不想给我说?广顺的眼皮翻了翻,又垂下了。祖父又大声说:广顺,你不想说,就滚,滚得远远的,再不要进我的院门了。
祖父站起来了,看样子,他准备走。
广顺乜斜了祖父一眼,他的腰板挺了挺,似乎要把他的胆量和勇气从腔子里拉出来,拉直。他仰起了头,目光避过祖父,面对着挂在中堂的祖上的那幅颜色发黄的画像说:
我去来,就是去来。
我把你这个瞎东西!
祖父话一落点,一把抓起搁在方桌上的烟锅就朝广顺打过去了。祖父出手特别快,广顺躲避不及,烟锅打在了他的额颅。刹那间,广顺的额颅上血流如注了。广顺没吭一声,狠狠地瞪了祖父一眼,走出了客厅。从广顺的额颅上滴下来的鲜红的血如同梅花的花瓣一样一路点下去,从我家的院子里一直点到了街道上……祖父的四十岁生日染上了血腥之气。这是一九四九年农历三月十四日的午饭之后。
我们那里人把过生日叫做寿——往往是由晚辈给长辈做。穷人即使到了四五十岁也难得做一次寿,一是因为家里穷,铺排不起;二是因为结婚晚孩子小,无人来操办。富人家不太计较这个,孩子小就自己给自己做——二十多岁起做寿的大有人在。祖父三十岁生日时,祖母就撺掇祖父做寿,祖父没有。那时候,祖父正在创家业,他知道,要在松陵村做大财东就来不得半点张扬,必须夹着尾巴做人低调处理自己。在祖父看来,只有穷人才享受消费的快乐,富人永远处在积累财富的愉悦中。祖父的家业是用他的不停歇的劳作和苦涩的汗水堆砌起来的。他一天可以割二亩八分麦子;进山割青草,他一次担两个担子,这一担草向前担一段路又回头去担那一担。他的耐力大得惊人,去半坡里犁地,一天不吃一顿饭不喝一口水。祖父是一个很优秀的木匠,他的木工活儿和泥水活儿一样出色。每年,田地里的活儿安顿好之后祖父就背着木匠家具串乡走村,给人家盖房、打家具或者做棺材去了。他将挣到手的钱一分一分地攒起来,一分一分地买回来土地,种上粮食,又将打到包里的粮食一口袋一口袋粜出去,用得来的钱再买地。祖父的土地就是这样由一亩变成五亩,由五亩变成十亩,由十亩变成了百亩。祖母活着的时候给我说过,三伏天,祖父托着犁去犁麦茬地,犁铧一插进地里,他就将鞋脱下来别在裤腰带上了,他宁肯将脚磨烂,也不肯将鞋穿烂。走在路上,碰见一堆牛粪,祖父就会用手掬进草帽,端上,倒进自己的地里去。祖父外出做木工活儿,临走时,他将十天或半月内家里人要吃的盐和醋用木勺子量好交给祖母,剩余的用铜锁锁起来,谁也不准动用——哪怕家里人没调料吃,他也不管。辣椒数着角儿吃,十天留十个辣椒,连一个也不多留。家里一百多亩土地,只雇广顺和来娃两个长工,收种时节,活儿紧了,就请短工,地里和场里的活儿安顿好之后就将短工辞掉了。
祖父对土地对庄稼对钱财对家里每个人的行为操守包括两个长工的为人嗅觉灵敏得如同弹簧一样,而对时局的变化却十分迟钝。松陵村以外发生了什么事,祖父从不关心。祖父总以为他种地纳粮雇长工收租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祖父总想把家业做大,不然,到了一九四九年正月,一些富人已将长工辞掉将土地卖得只剩下养家糊口的几亩薄地之时,祖父还买回来了六分庄南的一等地。祖父的家业殷实了,四十岁这年,不用祖母撺掇,第一次大模大样地给自己做寿。
祖父的生日恰巧在周公庙的庙会期间。松陵村距离周公庙只有一里半路,亲戚们和村里人早晨坐毕席都去周公庙看戏了。午饭前,在厨房里忙活的厨师吆喝着叫人绞一担水来,祖父就喊广顺,前院后院地喊,不见广顺。祖父以为,广顺也看戏去了。祖父心里对广顺不悦,并没有流露出来,他自个儿掂起桶去绞水。绞了一桶水提进灶房里,隔壁来帮灶的女人给祖父说:你去叫广顺,自己绞啥水?祖父说:广顺怕是看戏去了。那女人说:没有呀,我刚才去马房里倒水,他在马房炕上睡着哩。祖父放下水桶到马房去一看,广顺果然酣然大睡在马房炕上。当时,祖父还不知道广顺死睡的原因,就将广顺喊起来绞水。
吃午饭的时候,家族里一个和祖父同辈的人告诉祖父:广顺每天晚上去周公庙“撵香头”。祖父一听,筷子掉在了地上。他拾起筷子,笑着说:不会吧,广顺咋能去干那号事?家族里的同辈人只是给祖父透露了一个信息,没有和祖父争辩广顺是否去“撵香头。”
本来,祖父在他生日这天不会因为广顺去“撵香头”而发火的。尽管,他得知这个消息后十分生气,却一直忍着,准备过几天再查问是真是假。吃罢晌午饭,好多远路上的客人都走了,如果是在往常,广顺会主动地去收拾席桌,拆锅打灶——院子里的锅灶是临时盘起来的。可是,刚吃毕中午饭,广顺又到偏院里的马房里睡觉去了。祖父吩咐来娃去到马房里喊广顺。广顺来了,祖父一看广顺蔫头耷脑没有精神,相信广顺去“撵香头”的话八成是真的,不然,他不会像霜杀了的麦苗一样的。在祖父的眼里,只有那些“剌条”和地痞二流子才去“撵香头”,正派的庄稼人是不会干那号事的。在祖父看来,“撵香头”和嫖人家的女人是一回事,只不过冠冕堂皇罢了。
祖父算是把“撵香头”这件事看透了。人世间的事情是不能看透的,一旦看透,仿佛把人剥了皮,血淋淋的,惨不忍睹。“撵香头”本来是周公庙庙会上的一桩肃穆而神圣的事情。周公庙的庙会也是祈子会,那几天,四乡八村的年轻女人们由婆婆姐妹或姨妈姑姑带着前来祈子,她们在姜嫄圣母(人类始祖)殿前给“娘娘婆”烧了香,叩了头,许了愿,晚上,在皎洁的月光下手执一根点燃的香头游走于庙内的稠人广众之中,物色面目俊秀身体强壮的男人。一旦有男人被女人物色中,这女人便擎着香头走动,引诱男人上钩。这男人撵着香头,撵到东庵或西庵的崖畔下,崖畔下有一排不太大的窑洞,窑内早有人铺上了麦草供祈子的女人和她看中的男人野合。
男人撵到窑洞前,女人将香插在窑门外的一堆黄土上——表示里面有人。男人跟女人进了窑洞,两个人不问姓名不问籍贯不问年龄,宽衣解带,轻车熟路地在麦草铺上颠鸾倒凤、翻江倒海地干起了男女之事。事毕,女人满心喜悦地出了窑洞回到了亲人跟前——求子的壮举便悄然完成了。周公庙附近村庄里的年轻人深谙看似肃然而庄重的祈子活动中所包含的浪漫得近乎荒唐的、甜丝丝的内容。每年三月初九逢庙会,他们到庙会上去向女人堆里钻。而那些规规矩矩的小伙子明知“撵香头”就是嫖女人却从不动兴,他们有碍于家规家教有碍于有妻室不说,也不愿意把自己的种子乱撒在陌生女人的田地里去发芽、生根、结果。那些风流成性的年轻人“撵香头”上了瘾,庙会结束之后,不安分守己了,在村子里专门物色漂亮女人去嫖,惯上了瞎毛病。祖父担心的就是这个,他怕广顺“撵香头“后不走正道,成为一个职业嫖客。
从十九岁起,广顺就给我们家当长工,到一九四九年,广顺给祖父当了七年长工了。在祖父的眼里,广顺是一个地地道道老老实实的庄稼人,庄稼活儿样样精通,恪守着做人的规矩。祖父待广顺不薄,该给的工钱一个子儿也不少,逢年过节另外给广顺几斗麦子几斤菜油。祖父从未开口骂过广顺,更没有动过广顺一根指头。祖父用烟锅敲广顺,广顺没有料到不说,连祖父自己也吃惊——他确实被广顺的“撵香头”惹怒了:松陵村最好的年轻人如山一样在祖父心中塌去了一个角。广顺不是没有尝过女人是啥滋味。三年前由祖父一手操办给广顺结了婚,十分吝啬的祖父咬咬牙把八石麦子白白送给广顺做了聘礼。广顺的媳妇是祖父的一个木匠徒弟的妹妹,人长得体面不说,里里外外的活儿都能干。祖父大概这样想:我把媳妇给你娶进门,女人伺候不了你?你还去“撵香头”?嫖女人是祖父难以容忍的事情,他做人心中有自己的“礼”数。
晚上,祖父怀里揣着治破伤的白药,手里提着一个竹篾笼子,笼子里盛着亲戚们送来的两个“寿桃”,一斤点心一包挂面,他来到了村子西头,走进了广顺家。祖父一来是为了看看广顺,二来是为了给广顺媳妇打个遮掩——千万不能让女人知道广顺是因为去“撵香头”而挨了祖父一烟锅。
其实,广顺去“撵香头”也是事出有因。广顺是个秦腔迷。三月初九晚唱第一台戏,广顺给祖父打了个招呼就去看戏了,看毕夜戏回来的路上,村子里一个叫狗旦的年轻人给广顺说,他去“撵香头”来,广顺说:你咋能干那号事?狗旦说:那事比吃肉还香哩。广顺说:去去去,不嫌丢人?狗旦说:丢啥人?你想撵还撵不上哩。广顺说:叫我撵,我也不去撵。狗旦说:你撵不上,才说大话哩。广顺说:咱打个赌,输赢是一捆麻花儿。当时,广顺只是为了赢一捆麻花吃。三月初十晚上,狗旦眼看着广顺被一个女人领进了东庵下的一眼窑洞。撵了一次香头,广顺尝到了比“吃肉还香”的味道,他觉得,不能做的事一旦做了,也就做了,并没有带来什么坏处。一连四个晚上,他借看夜戏之名去“撵香头”,到了三月十四晚上,祖父生日那天他实在是筋疲力尽了。
祖父一进院门故意干咳了一声。广顺媳妇一听有人进来了,撩起门帘,出了房间。她一看是祖父,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祖父进了房子,广顺从炕上起来了。他的额颅用白条子布勒着。祖父正在寻思怎么向女人开口,女人却先说话了:三哥,你看他,二十五六了,还那么冒失,怎么把头就磕在槽头上了?祖父一听,广顺已给女人撒了谎,也就放心了,他说:也怪我,晌午叫他多喝了几盅,他去给骡子拌草,可能不小心栽倒了。女人说:哪能怪三哥?怪他自己粗心。广顺垂下头一句话也不说,他连续嫖了四个晚上女人,哄起自己的媳妇来天衣无缝。祖父说:广顺,你明天再歇一天,我和来娃去种稻黍。广顺说:我能行。祖父说:不要犟,你再歇一天。祖父为不自觉地参与到哄广顺媳妇的勾当里去而羞愧难当,他不愿意在广顺家里久留,掏出白药,放下礼物,提着空笼子回去了。
第三天,祖父和广顺在一块地里种稻黍。歇晌的时候祖父说:广顺,我前日个冒手了。广顺说:你是掌柜的。祖父说:我是你三哥,我是怕你……广顺说:你那一烟锅把我打灵醒了。祖父以为,他那一烟锅是为了打掉广顺的坏毛病——你再嫖女人就打断你的一条腿;祖父以为他打广顺只是三哥教训七弟。然而,事情并非祖父所想的那样简单。
3
事过三个月后的农历七月十四日,凤山县解放了。没多久,土改工作组到了松陵村。松陵村的土地改革像三伏天的天气一样热烈。我们家被定为地主成分,祖父和祖母都戴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在土改中,贫农冯广顺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他分得了土地和牲畜不说,我家偏院里的三间马房也分到了广顺名下。
刚分到“果实”的广顺和祖父之间的关系显得有点别扭。他似乎觉得他不该白白地到我们家装粮食搬家具牵牲口;他似乎觉得他的作为对不起一向对他很宽厚的三哥。临拆马房的前一天晚上,广顺来找祖父。广顺进了房间,蹲在脚地,叫了祖父一声三哥,半晌不开口。祖父说:广顺,你现在是贫农,到这个院子还是少来几次好。广顺说:三哥,你说这话比用烟锅敲我还难受。又是烟锅?祖父看了广顺一眼,心头一阵悸动——广顺额颅上的疤痕太显眼了,它成了祖父一块心病。祖父不再说什么了。广顺说:我知道那三间马房是你挣来的,不是我……广顺欲言又止了。他想说,不是我白占你房。他欲求祖父谅解。祖父说:广顺,分给你就是你的了,你不要再说了,啥时候拆,你说一声,我把里面的旧家具搬出来。广顺说:三哥到底是明白人。我明天拆房。祖父说:那好啊,你拆吧,我今晚就去搬家具。广顺说:三哥,我不是来逼你的。就算你把那三间马房典给我了。祖父说:广顺,你千万不要那么说,你那么说,工作组知道了,非斗争我不可。广顺叫了一声三哥,竟然不知说什么好,脸上那愧疚的神情久久不肯撤走。
广顺的那头骡子是从我家分去的。秋天里他给自己种上麦子之后将骡子吆到了我们家的地里。祖父只剩下了一头老牛和一头牛犊,一晌午种不了几分地。祖父宁愿自己慢慢种地也不愿意广顺来当帮工。广顺一进地,祖父就支使他却支使不开。广顺帮祖父种了两天地。为这件事,广顺被工作组叫去谈话了。工作组先是批评广顺,之后,又开导他——他现在是松陵村的主人,而不是冯巩德的长工了。广顺自然给工作组做了检讨。
冬天里,广顺被派到乡政府学习。广顺从乡政府回来,再没有到我们家去过。第二年春天,广顺入了党,他在街道上碰见祖父不再叫三哥了。
一九五一年,“三反”开始以后,在斗争地主分子的大会上,广顺第一个上台控诉。他指指点点,声泪俱下,控诉祖父如何打骂长工、不把长工当人看。广顺指着额颅上的疤痕说,祖父过生日时嫌他没送礼,一烟锅把他打倒在地了——广顺闭口不提他“撵香头”的事。
广顺还揭发了祖父在土改中向他行贿的事。广顺说得有鼻子有眼。其实,究竟是怎么回事,广顺和祖父心里都清楚。祖父听说要分浮财了就去找广顺。祖父不是为了求广顺什么的,广顺不是农会主席,不是村干部,求他也无用。祖父只是为了向广顺掏掏心里话——他想叫工作组给他多留一些房屋。祖父给广顺说了这个意思,广顺知道自己无权过问,宽慰了祖父几句。祖父去广顺家里时顺手拿了一包挂面——两年后,广顺将那包挂面作为祖父行贿的把柄揭发了。
当年的主人变成了敌人,当年的长工成了松陵村的主人。一九五三年,广顺当上了松陵村的党支部书记,一直当到了一九八三年。从此,祖父成了广顺的斗争对象。
还是因为广顺额颅上的那块疤痕。
那是一九六二年的周公庙庙会期间。三月十四日,广顺到了庙会上,他走到了当年和女人们快活过的窑洞前(“撵香头”的习俗解放后被废除了),看着被蒿草蓬住的窑洞口,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晚上,和他在这眼窑洞内交欢的女人极其丰满,那女人给他带来了难以言喻的销魂。他们刚一进窑洞,女人就把她的舌头填在他的嘴里了,她几次把他浪在愉悦的巅峰,久久不肯落下来。事毕,她嘤嘤地哭了。他以为,她后悔了。她却哭着说,我的娃长大后还不知道他的爹姓啥呢?他明白了,她要他的名字。他在她的脸蛋上亲了一口,说:姓驴。女人吭地笑了。他不能犯忌,爬起来就走。如今,人去物非,他未免伤感。广顺正在愣怔地出神,一个道士模样的人走过来了,道士看了看广顺说:给你看个面相吧。广顺说:我不信那一套。道士说:不要你一分钱。广顺说:不要钱也不看。广顺已经抬脚走开了,那道士不依不饶地撵在他的身后,广顺躁了,回过头来说:你想干啥?道士说:不想干啥。恕我多两句嘴,你本来是一副福相,四方脸,鼻梁直,耳朵大,前庭饱满,要命的是你破了相,你的坏运气就在额头的那块疤上,你的后半生……不等道士说下去,广顺拧身走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额颅上的疤痕不但没有隐去,反而越洇越明晰了。广顺不愿照镜子,广顺一旦从镜子里看见那块疤就将镜子摔碎了,仿佛那块疤是他的人生的屈辱和羞耻的记录。洗脸时,他的双手要从那块疤上绕过去,他一旦触到那块疤,手指头好像放在了火中烤——对祖父的夙怨触手可及。道士的话如同一把大手把广顺压在心中不想提的那根蔓很伤情地提起来了。可是,他不相信“破相”的话,更不相信相貌的差异会给人带来好运或厄运。他的二儿子刚满一岁就得了小儿麻痹,他的一个女儿生下来就又聋又哑,有人劝他去周公庙给“神”烧些香,许个愿。他不去。他没有给人下过跪,他更不愿意给神下跪了。广顺摆脱了道士,到东面的舞台下看了一会儿戏,又想到西面的舞台下去看戏。他刚钻出人群,老远看见有一个女人正在朝木桥上走去,那女人迈着碎步,脚下轻得像水上漂一样。广顺眼睛一亮:这女人太像他当年在月夜里追撵的女人了。广顺兴头来了,几乎是小跑着向木桥那边而去。他估摸,不等那女人上桥,他就会追上她,看个究竟的。突然,被他摆脱掉的那个道士仿佛一杆长矛横刺过来了,道士挡住了他的去路:咋样?给你看个相吧?他恶狠狠地瞪了道士一眼:走开!道士说:看你,害怕啥?他高叫一声:滚!一把将道士推开,三步并作两步跨上了木桥。过了木桥,他再也没有瞧见那个女人。
广顺回到家的时候,女人正在院里用簸箕簸麦子。女人一看见他,脸拉下来就问他:你咋回来这么早?他劈头问女人:你看我咋样?他用手指了指面目,女人觉得他问得蹊跷,停下了簸箕:都结婚这么多年了,还叫我看啥?他说:叫你看,你就看。女人盯了他一眼:好着哩。他说:说实话。女人说:有点阴。他说:不是说这个。他的一只手指头在额颅的疤痕上点了点。女人说:这疤痕碍你啥事?他说:得是这叫破相?女人说:我也闹不清,反正,面目不浑全了。他掉过头用生硬的目光盯住女人喝问道:你也相信破相?女人惊恐不安地说:你今日个咋啦?他说:我不相信破相,不相信求神问卦那一套,啥也不相信。女人说:你不信就不信,给我凶啥哩?女人不知道他心里埋藏着什么。
广顺确实不相信道士的话,可是,道士的那句话勾起了他对往事的记忆,勾起了当年的屈辱和对祖父的仇恨。当天晚上,广顺就召开斗争会,斗争祖父。在那天晚上的斗争会上,广顺第一次动手打了祖父。在此之前,祖父被斗争了好多回,广顺从未动过手,而且,一旦有人出手,广顺就对那些人喊三喝四,不准他们胡来。第一次打祖父,广顺打得很狠,他又是拳打脚踢又是扇耳光,他逼着祖父,要祖父交出“变天账”。祖父争辩了两句,广顺就举起了屁股底下的凳子。就在凳子将要砸下去的一瞬间,公社里派来的驻队干部挡了他一把,凳子打在了地上,两条腿被打飞了。不然,祖父非被广顺砸死不可。
广顺和祖父之间,不只是个人恩怨。作为一名基层干部,广顺对阶级敌人绝不心慈手软。在一九六四年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广顺一手操纵给松陵村补定了十四户地主。一个年仅二十九岁的年轻农民因为被戴上了地主“帽子”而自杀,广顺对死人也不放过,在棺材前召开了他的批斗会。陪斗的祖父回家后对父亲说:广顺年轻时不是那样的。父亲说:人是会变的。祖父说:是啊,世事变了,广顺不跟着变由不得他。
做了地主的祖父从不把被人斗争当做一回事。参加斗争会回来,他照常吃照常睡。月黑风旺的夜晚,祖父到各生产队去送通知,有一次,他从饮牛沟里跌下去,磕磕绊绊地回来时,已是鸡叫三遍了,第二天照常起来劳动。下雨天,广顺派祖父去公社里送材料,年过半百的祖父戴一顶发黑的草帽,迎着倾盆大雨出了村子,回来时,一身水一身泥,他连一声叹息也没有。
祖父终究有倒下去的一天。
那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变着法儿整治祖父,祖父由两个年轻人赶着跑步,从一队跑到二队,由二队跑到三队……祖父实在跑不动了,两个年轻人就搀着他跑。年过六十的祖父跑掉了鞋,一双精脚还得跑;裤带掉了,裤子拖到了脚踝上,光屁股亮出来了,两个年轻人不让他提裤子,继续架着他跑……祖父终于跌爬在地上起不来了。父亲和叔父将祖父抬回了家。祖父真能活!他躺了一天,又恢复了元气,他拿起烟锅,吃了一锅烟,他在炕边上磕着烟锅,只磕了一下,祖父不磕了,不知怎么的,他突然想起了过去的事情,祖父说:我不该敲他一烟锅。父亲说:事情过去多年了,你还没有忘记?祖父说:广顺的额颅还在,我咋能忘记呢?祖父说:说实话,我不愿意看见广顺的额颅。父亲大概明白,祖父是怎么想的,也就没再吭声。
4
一九七九年,七十岁的祖父第二次给自己大摆寿席。
三十年来,祖父从未光明正大地给自己做过一次寿。每年农历三月十四日,祖母总是要念叨一遍:今日个是你的生日。祖父只是苦笑一声:又老了一岁。祖父从未动过做生日的念头。到了三月十四日,祖母大不了给祖父做一顿臊子面吃(有时候,连臊子面也吃不起),亲戚邻人不来祝寿,祖父也不敢请他们来。
祖父这一次做寿,无疑是做给松陵村人看的。
三月初,祖父就放出话,他要借过生日好好地款待一次松陵村人。
祖父的做寿将松陵村的一些人推向了两难境地:去祝寿还是不去?虽然,广顺已在社员大会上宣布:地主分子的改造已经完成。可是,一纸文件很难于一夜之间改变人们已经固定了多年的观念,在许多庄稼人的心目中,祖父冯巩德还是地主分子——即使现在不是,说不定,过几年世事翻过去,又是了。贫下中农咋能去给地主祝寿呢?地主就是敌人。难道一个文件能将地主变成人民?三十年了,松陵村的庄稼人一直生活在和阶级敌人斗争的岁月里。没有敌人的日子怎么过,他们不可想象。
杀了猪,请了厨师,还请来了南堡公社的戏班子。祖父依然放心不下的是:做好的酒席没人来吃。
三月十四日这天是祖父忐忑不安地迎来的。天还没有亮透,祖父就起来了,他孤单单地站在院门外迎接前来给他祝寿的松陵村人。祖父苦苦地等了一个多小时,踏着晨曦第一个走来的竟然是斗争了他多年的生产队长,祖父脸上的焦虑换成了笑颜,他给生产队长递了一支烟,点上了火,将他让进了院门。使祖父感到意外并且欣喜不已的是,前来祝寿的松陵村人比他估计的还要多,不仅冯姓的人来给他祝寿,张姓、田姓、李姓、刘姓的人也来给他祝寿了(尽管一些贫下中农没有来)。祝寿的松陵村人老远喊着三爷、三伯、三叔、三哥,喊声喊得祖父心里大概用蜜蜜了一般,他脸庞上的笑容如同印在白纸上的铅字一样久久没有撤掉。
客人来了一院子,父亲和叔父催着祖父开席,祖父说:再等一等。父亲和叔父还不明白,祖父在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松陵村的党支部书记冯广顺。可以说,祖父的席桌是摆给广顺的,广顺来不来祝寿,至关重要。祖父残留的岁月怎么度过和广顺密不可分。
当广顺的女人听说祖父要做寿之后第一个把这消息带给了广顺:你去不去?广顺没有正面回答女人,反问道:你说去不去?女人当然希望广顺去,但她不敢多嘴,也就没表示看法。
三月十三日晚上,广顺从大队里开会回来时,女人还没有睡,女人在等待广顺的回答。广顺要上炕睡觉,女人耐不住就问他:你明日个到底去不去?广顺又反问女人:你说呢?女人不想表露自己的心迹,嗫嗫嚅嚅道:他是,他是地主……广顺突然变得很凶:胡说!他是地主也要去。你知道不知道冯巩德现在不是地主了?女人不知道广顺为什么要发躁,就闭上了嘴。即使广顺把自己的复杂心情写得满脸都是,女人未必能读出来。女人只知道下地劳动,只知道生儿育女,她不知道,几十年的基层干部生涯已将广顺练出来了,练就了广顺对付人的一套方法,练出了广顺洞察世事的眼光,练出了他假话真说、真话假说的本领。
祖父眼巴巴地看着村子西头。
当祖父看见广顺昂首阔步地朝他走来之时,眼睛亮了。祖父站不住了,他准备去迎接广顺,但他向前只走了两步,又退回来了。他站在原地,胸脯挺了挺,好像真的要在广顺面前挺出一副当年的地主派头。广顺步履沉稳地走过来了,广顺走到祖父跟前,叫了一声三哥。三十年了,广顺第一次叫祖父三哥。祖父拉住了广顺的一只手,广顺随之也把另一只手伸过来了,于是,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这是两双强有力的手,这是两双个性鲜明的手;这两双手分别很艰难、也很潇洒地书写过各自辉煌或屈辱的人生史。这两个站在不同阵营里的强汉子,两个做了三十年敌人的庄稼人在春天里一个早晨走在了一起站在了一起一双手握在了一起。广顺先开了口,他不再像呵斥牲口一样呵斥祖父了,他面带着笑说:三哥,给你祝寿。祖父说:冯书记,快入席,大家都在等你哩。三十年来,很少进地主家院门的冯广顺大模大样地跨出了坚定不移的步子。
广顺和祖父坐在同一张席桌上共用一桌饭,使在座的松陵村人不由得注目:他们几十年来第一次目睹这样的情景。他们大概想不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化会在一个早晨完成,他们从广顺和祖父身上感觉到世事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人们一边吃一边唧唧喳喳地议论:广顺斗争了祖父半辈子,顶什么用呢?斗来斗去,如今两个人还是平起平坐了。广顺当然能听见人们在说什么。他举着酒杯说:我敬三哥一杯,祝三哥健康长寿!祖父站起来了,同桌的人站起来了。祖父捏住酒杯的手颤抖着,酒水从酒杯里撒出来了,他和广顺碰了杯,连声说:高兴,高兴。冯书记喝,大家都喝。
祖父的第二次做寿,做得恰到好处。祖父要的就是这个结果:大家高兴,自己荣耀。
那天,广顺确实是喝多了。回到家,他栽倒在炕上,不住地喊叫祖父:冯巩德啊冯巩德!我把你这个冯巩德!他一喊叫,额颅上的疤痕就向一块缩。女人问他:三哥怎么了?广顺说:冯巩德还是比我有能耐。说罢,双手捂住了脸,额颅上的那块疤没有被捂住,显得有些狰狞。
广顺是很精明的。他能在松陵村经营这么多年和他的能识事务分不开:查田定产,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农村社教,“文化大革命”,每一次运动来了,他都跟着跑,绝不做绊脚石。他明白,当潮流涌过来的时候,他一个人是挡不住的,他不可能不被卷走。而这一次叫他和他的敌人平起平坐,他出了一身汗,脱了一层皮才想通了:他要在松陵村继续经营下去就必须跟着世事走,这并不是他感情上能否接受的问题,不接受也得接受,不然,他就没戏了。
广顺也有执迷不悟的时候。
一九八三年搞生产责任制,广顺以对抗的姿态出现在松陵村。他一听,要他领导农民解散生产队,他坚决不干。这一次,不是广顺跟不上趟,他不跟趟了。在他看来,解散生产队不比给地主摘帽子,不比改正成分和退赔财产,解散生产队就等于把过去的事彻底否定了,等于自己打自己嘴巴。他给工作组长说,他不愿意在松陵村走资本主义,谁愿意走,让走去,他不干了。广顺以为,他是几十年的老干部了,他这么一闹,公社党委书记会给他做工作说好话,推着他走的,或者向他妥协。可是,没人找他谈一次话,一纸红头文件,把他免职了。他的干部生涯就这么仓促地结束了。这是他没有预料到的事情。
不当干部以后,广顺朝我们家跑得勤了,他差不多每天晚上要来和祖父说闲话。两个人天南地北,东拉西扯,什么话都说,就是不说他们曾经做敌人的话。
5
祖父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会像干部一样每月领取人民政府的二百元,而且是白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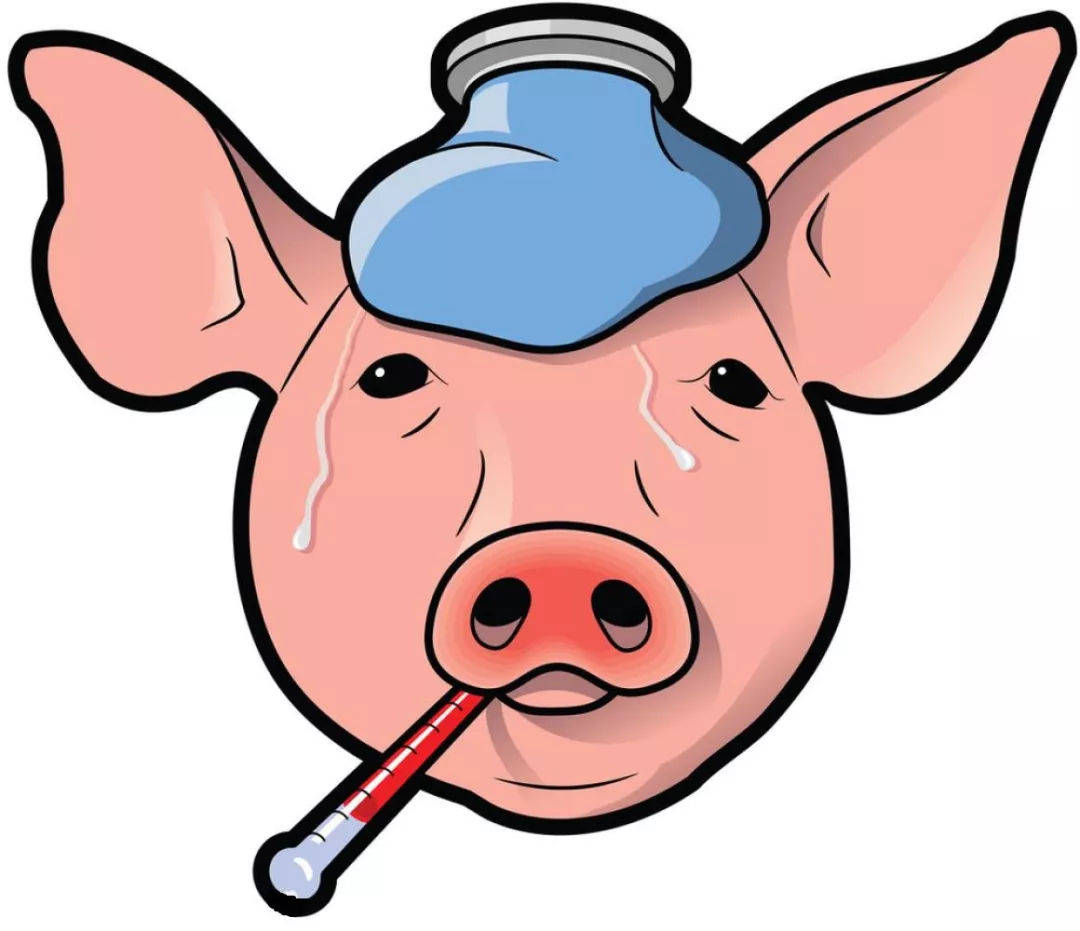
一九九三年,凤山县人民政府在全县搞“老寿星”活动。他们先是将“老寿星”的年龄定为一百岁,经过调查摸底,全县没有一个百岁老人。后来,将年龄定为九十岁,而全县九十岁的老人只有三个。于是,就把“老寿星”降为八十五岁了。就在那一年,祖父作为南堡乡松陵村唯一一个“老寿星”进了县城。祖父披红戴花,坐在了县礼堂的主席台上。凤山县县委书记和县长与祖父握手照相,表示祝贺。祖父有生以来第一次上了电视。按照凤山县人民政府的有关文件精神,祖父每月得到了二百元人民币的补贴。
然而,这二百元人民币却成了祖父的一块心病了。他第一次领回来钱,一分没有花,存在了村里的信用社。他郑重其事地给父亲说他不能领那钱。父亲问他为啥。祖父说:我不缺钱花。父亲说:这是人民政府对老年人的关怀,不是你缺钱不缺钱的事情。祖父说:关怀也不能关怀到我的头上来呀,过去给咱村拨下来的照顾款都是给贫下中农的,我算个啥?我咋能白领政府的钱?父亲说:这不是照顾款,这是补贴,谁高寿就补贴谁。祖父说:不论是啥款,都是政府的钱,我不能白领政府的钱。你去给村长说,把这钱给你七爸,广顺把日子过烂散了。父亲说:七爸不是老寿星。祖父说:他穷,政府应当接济穷人。
祖父的话没有错,广顺确实成为松陵村最穷的农民了。
广顺有三个儿子。患小儿麻痹的二儿子十三岁那年扑到崖下去摔死了。大儿子福奇的两个儿子因偷盗、抢劫被判了刑,福奇到广东打工去了。广顺和三儿子孝奇在一块儿过日子。两年前,孝奇领着邻村的一个女孩儿私奔了,家里的责任田撂给了广顺和孝奇的媳妇翠翠。广顺年过七十了,依旧要去责任田里劳动。家成了这个样子,日子越过越穷,这究竟怪谁?广顺也懒得去想。支撑他活下去的不是思想不是情绪而是不停歇地去责任田里劳动。他的腰佝偻了,脸像树皮一样,瘦骨嶙岣。他比祖父小十四岁,看起来,比祖父苍老得多。
做了“老寿星”的祖父未免在松陵村招来一些闲言碎语。父亲就听见,有些人这样议论:“过去的照顾款是给穷人的,现在,政府不爱穷人了,尽给富人干好事。”“这世事就怪了,翻过来,倒过去,都是富人的天下。”有一个好吃懒做的二杆子在一天午后把祖父拦在街道上,高喉咙大嗓子地说:老汉,你当地主时一天也要干三晌,现在躺在炕上白领共产党的钱,你咋那么漂(美)呀?祖父听罢,只是一笑:你能活到我这岁数,也躺在炕上领钱哩。那二杆子货并不知道,祖父领二百元心里并不安然。再说,祖父也不少那二百元,父亲开石灰厂,叔父办农场,两个人每年的收入几十万,还愁那二百元吗?连祖父自己也没料到,他晚年会有如此福分。看来,人的命运并非能掌握在自己手中。
广顺照常每天和祖父来拉话。广顺吃祖父给的纸烟,祖父吃他的旱烟。两个老人无话不谈。广顺临走时,祖父二十块钱给过,五十块给过,一百块也给过。开初,广顺推推拒拒地不接。这毕竟不比当年逢年过节时祖父给他的口袋里灌麦子,那是祖父对他的劳动奖励,而现在祖父给他钱花,是对他的同情怜悯。广顺老是老了,心里很亮清。当然,祖父能看出个广顺是啥心思。祖父说:老七,人活到哪里,说哪里的话,活瞎了,就从瞎处来,腰杆挺得再硬,没有一口饭吃不行。广顺咕地咽一口唾沫,仿佛是咽下去溢上来的苦味儿,他说:三哥呀,雀儿也有指甲盖大的脸,我真个活得没脸了。祖父说:老七,你千万不要那么想,如今的世事和以往不同了,你要跟着世事走。广顺苦笑一声,点点头,他大概只是在心里说:是的,如今笑贫不笑娼,他还顾忌什么呢?钱是硬头货,他七十多岁的人了,到哪里去挣钱?广顺从祖父手里接过去钱,叫了一声三哥,老泪纵横了。
6
祖父九十二岁的生日比哪一次都过得排场。院子里搭了一个席棚,街道上搭了一个席棚,一次就可以坐二十桌客人。早晨六点就开始坐第一拨席。不仅松陵村人来给祖父祝寿,南堡乡政府的李乡长和乡党委王书记也来了。凤山县政协和凤山县民政局来了领导不说,还给祖父做了匾。小车停了半个街道。高音喇叭里的秦腔戏如同皎洁的月光一般给祖父的生日宴席上撒下了一派清辉,欢庆的气氛罩住了松陵村。
第二拨席坐毕,祖父坐不住了,他在院子里的席棚中看看,又去街道上的席棚中看。吃饭的客人一看见祖父都站起来说:祝老寿星长命百岁。祖父笑着说:大家吃好,喝好。父亲一看祖父在席棚中,就对祖父说:爹,你去躺椅上躺着,县政协王副主席打来电话说,等一会儿要来。祖父说:知道了,我看看,谁还没有来。
其实,祖父只是在找广顺。
第三拨席坐上了,广顺还没来。祖父没有给父亲打招呼,到村子西头找广顺去了。
这时候的广顺正坐在房间低头垂泪。前几天,广顺还在孝奇的媳妇跟前念叨给祖父祝寿的事。刚念叨毕,七岁的孙子病了,高烧发到了四十度。孙子在村医疗站吊了三天液体,广顺身上的钱花得光光精。那二百多元还是祖父给他的,他舍不得花,一直装在身上。清早起来,广顺踌躇再三:不去给祖父祝寿,他过意不去,也失了人情;要去祝寿,他连买一斤糕点的钱也没有,他失了面子。怎么办呢?广顺由此联想到自己破麻袋一样浑身是洞的日子,不由得伤心落泪了。
孝奇的媳妇翠翠还算贤慧,没有撂下两个孩子出走。
孝奇领上那女孩儿远走高飞之后,知书达理的广顺曾劝儿媳另嫁人算了。他知道他的儿子靠不住。公公这么一劝,儿媳反而不走了,她不忍心丢下两个孩子,也不愿意将公公一个人撂在家里(广顺的女人十年前就过世了),广顺就和儿媳硬支撑着这个家。庄稼人没有钱没法过日子。翠翠一看,村里有人在县城卖面皮能赚钱,就在家里学做面皮。面皮做好之后,由广顺拿到县城去卖。
广顺毕竟老了,笨手笨脚的,而且没做过生意,在县城跑了一个月,只净赚了二百多元。那天,街道办事处的人刚收过卫生费,城关镇政府的几个年轻人又来收卫生费了。广顺本来就没卖几个钱,憋着一肚子气。他一看,几个年轻人不讲理,硬箍住要钱,就指住他们,用粗话乱骂。那几个年轻人哪里吃他这一套,他们一拥而上,几脚将他的摊子踩烂了。广顺没再和年轻人辩理,他走进了县政府,叫着县长的名字,大骂一通,把几只尚好的碗碟和铁锅摔在县政府院里,回到松陵村,结束了他的第一次做生意。
当天晚上,广顺到我们家里来,把他骂县长的话给祖父学了一遍。广顺说:三哥,你看我还有啥活路?祖父没吭声,吃了一锅烟,磕了磕烟锅说:人只有把人不当人活才能活出样儿来。广顺咂着祖父递给他的纸烟,低下头去思忖……
祖父走进了广顺家的院门。
还是那豁豁牙牙的土墙,还是那硬挺的破旧的厦房,贫穷像瓦棱上的青草一样顽固地生长在这个家院里。祖父喊了两声广顺,上了厦房的台阶。翠翠上地去了,两个孙子去了学校,院子里寂然无声。祖父撩起门帘一看,广顺坐在炕沿默然垂泪。广顺一看是祖父,叫了一声三哥,哽咽得说不出话来了。祖父说:一个人坐在家淌啥眼泪?走,快去坐席。广顺说:我活得没脸见人了。祖父说:咋能说没脸见人?今日个没谁都行,没你老七不行,走吧。广顺说:三哥,你看我……他双手抖了抖,祖父似乎明白,他要说什么。祖父说:咱两个还计较那一斤点心?跟我走。
广顺跟着祖父来到了席棚中。广顺被祖父推到了上席。
吃毕早饭,广顺和祖父坐在院里说了一阵子话。广顺说他有点头晕,祖父以为是他喝了几口酒的缘故,就叫他回去了。

广顺是吃中午饭的时候“中风”的。
广顺坐的是第一拨席。和广顺坐同一桌席的几个老汉看见,广顺拿筷子的手有点犟,还以为他右臂有麻达。广顺拿起筷子,夹了几次,把菜夹不到筷子上。他勉勉强强地夹上了菜向胳肢窝戳了戳,没有送到嘴里去,就从凳子上溜下去了。祖父听见了人们的喊叫声之后,急忙向街道上的席棚中走。这时候,广顺已被一个年轻人抱起来了。祖父叫了一声广顺,广顺睁开眼看了看祖父,嘴张了张,说不出话来了。
广顺被年轻人背回了家。
祖父和父亲随之撵来了。父亲已吩咐人去村医疗站请牛医生。
不一会儿,牛医生背着出诊包来了。他给广顺量了量血压,听了听心脏,说广顺是脑溢血。祖父问牛医生:能不能去县医院?牛医生说:出血太多,不行了,恐怕耐活不到天黑了。快给他准备后事吧。广顺没有棺材没有老衣。翠翠在柜子里翻了翻,连一双半新不旧的袜子也没有。祖父给父亲说:你派几个人到县城去给你七爸买老衣抬棺材。父亲说:你不用操心,七爸的后事我来安排。
晚上,父亲给祖父请来的戏班子刚开了场,在欢快热烈的乐曲中,广顺咽了气。广顺临走前,祖父正守在他跟前——本来,他应该坐在戏场里去听戏。广顺闭上眼以后,祖父化了两张纸钱,他未给广顺盖遮脸纸之前看了看他,祖父叹息道:广顺呀,我不该打你一烟锅的,给你额颅上留下了个疤。几十年过去了。祖父还记着他那一烟锅。祖父是第二次提起陈年往事的。
广顺倒下头之后,父亲派人四处去找孝奇,找了三天,没有找见孝奇的人影儿。有人说,孝奇领着那个女孩儿卖淫被逮捕了;有人说,孝奇贩毒被同伙打死了。谁知道呢?大儿子福奇的电话倒是打通了,他借口自己生病回不来。村里人都说,福奇怕回来担负丧葬费故意不回来。谁知道呢?
父亲掏钱安葬了广顺。
安葬广顺那天,本该由儿子来摔“纸盆”(盛烧纸灰的瓦盆),既然儿子没在跟前,就由孙子来摔。按照我们那里的说法,儿子摔纸盆表示后继有人。纸盆一定要摔碎,越碎,表示人丁越旺盛。广顺七岁的孙子头顶着纸盆,由翠翠牵着手,走在送葬队伍中。到了村子外面十字路口,执事的叫广顺的孙子摔。广顺的孙子从头上取下来纸盆双手端着向棺材上摔去了,纸盆没有破,在地上圆圆地滚了一圈。翠翠一看,将纸盆拾起来交给儿子,吩咐儿子再摔,儿子第二次还是没有摔碎。这是村里人没有见过的事情。村里送葬的庄稼人不由得唏嘘感叹,亲人们的哭声更加悲凉了。祖父一看那情景,一声叹息,枯瘦的眼泪含在眼眶里,硬是没掉下来。
原载《延河》杂志2005年第6期转载《小说月服》杂志2005年第9期
作者简介:
冯积歧,1953年生于陕西省岐山县。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3年开始发表小说,在《人民文学》、《当代》、《上海文学》、《北京文学》等数十种报刊发表中短篇小说250多篇(部)。小说多次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杂志选载。多次入选各种优秀作品年选并多次获奖。出版长篇小说《沉默的季节》、《逃离》、《两个冬天,两个女人》等8部。长篇小说《村子》获陕西省“五个一”工程奖、柳青文学奖。
公众号ID
- 随机文章
- 热门文章
- 热评文章
- 中蜂夏天怎样繁殖快 中蜂夏天怎样繁殖快一点
- 高清养蜂场 养蜂场图片高清
- 兴旺村 兴旺村计划三天修一条水渠,第一天修了全长的
- 钱串子 钱串子多肉的养殖方法和注意事项
- 四棱豆 四棱豆根图片与功效
- 粽子馅 粽子馅料有哪几种
- 抓蜂王的正确方法 抓蜂王的正确方法图解
- 龟背竹 龟背竹怎么养才能更旺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