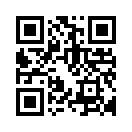亚欧大陆,是人类起源和早期发展的中心地带,也是早期文明的主要舞台。亚欧大陆各地理区域互相连属,却又因天然障碍而相对独立,自然环境千差万别,早期人类文化颇多共性而又异彩纷呈。如果着眼于文化多样性的一面,可将丝绸之路出现前全新世大部分时段的亚欧大陆[1],大致划分为三大文化圈,即以中国黄河和长江“大两河流域”为中心的“早期东方文化圈”,以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小两河流域”为中心的“早期西方文化圈”,以及东、西两大文化圈以北以亚欧草原为主体的“早期北方文化圈”(图一)。
图一 全新世亚欧大陆三大文化圈示意图
底图采用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发布的世界地图(1∶1亿,局部,审图号:GS[2016]2950号)
以往学术界早有亚欧大陆存在东、西两大文明中心的观点,并从宏观角度分别对东、西两大文化区进行过研究[2]。也有对北方亚欧草原地区的研究[3],有时称其为“内欧亚(Inner Eurasia)”[4]。但从全局角度讨论三大文化圈者还很少见[5]。有些学者提出青铜时代“欧亚”[6],青铜时代“世界体系”或者史前“全球化”这样的概念[7],其实质不过是强调早期西方文化通过亚欧草原的东向拓展,由于较少考虑北方文化圈本身的文化基础,也几乎完全忽略了东方文化圈的西向作用,所以这样的“欧亚”、“世界体系”,主要还局限在西方文化圈的范围。
本文拟以陶容器为主要依据,结合其他遗存状况,对三大文化圈的范围、特征和发展脉络略作讨论。自新石器时代以后,陶容器在亚欧大陆分布颇为普遍,形态复杂多样,敏感易变,而且很大程度上能够体现当时人群的生活习俗,这是本文将其作为首要依据的原因。但陶容器等因素并非同时出现于亚欧各地,其起源、发展、传播、交流的过程颇为复杂,因此不同时期三大文化圈的范围自然会有一定变化。此外,由于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三大文化圈之间还存在较大范围的交汇区域。
一、早期东方文化圈
早期东方文化圈的地理范围,中心在黄河、长江流域,主体是涵盖中国大部地区的“早期中国文化圈”[8],东南包括东南亚及太平洋诸岛屿,东部涉及朝鲜半岛和日本岛,北向波及亚欧草原,西向触及中亚。
东亚陶容器最早发现于华南地区(包括长江流域南缘),已有两万年左右历史[9]。这些世界上最早的陶器基本都是圜底的釜、罐类,不少在制作时留下绳纹,或许与模仿或者依托编织物制陶有关。约公元前9000年以后,面貌各异的陶器开始在中国中东部扩展开来,尤以长江下游上山文化素雅的圈足盘、豆、壶等最为复杂精致;上山文化陶器多着艳丽红衣,甚至出现简单的白色和红色彩,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彩陶。虽然后来长江流域及其以北的陶器形态和华南不尽相同,但很可能都是在华南陶器启示影响下所产生[10],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向四周拓展。中国还是稻作和粟作农业的发源地。水稻在长江流域南缘的栽培可能有15000年以上的历史[11],黍在华北地区的栽培历史也应该在10000年以上[12],随后向四周的狩猎采集区域传播,逐步形成“南稻北粟”的农业格局。至公元前4000年左右,在长江、黄河和辽河流域大部地区,农业经济已成主体。家猪的饲养也至少可早到距今9000年以前[13],后来在大江南北广泛分布。
展开全文
陶器和农作物的传播,有着大体一致的范围和路线。
1.向北 庙底沟式的花瓣纹彩陶于公元前4000年之后,到达内蒙古中南部北缘,甚至不排除到蒙古东南部的可能性。粟作农业也有传播至这些地区的可能。公元前1500年以后,源于中国北方地区的陶鬲则最北见于蒙古中东部和外贝加尔地区[14]。
2.向东北 后冈式陶器于公元前5000年后到达西辽河流域[15],最远到达第二松花江流域[16]。公元前3000年后大汶口-龙山风格陶器出现在朝鲜半岛北部[17],大汶口式的螺旋纹陶器装饰一度见于黑龙江下游[18]。公元前2000年后陶鬲见于嫩江流域[19]。粟作农业公元前6000年左右已经出现于西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20],公元前3000多年抵达朝鲜半岛。
3.向东南 约公元前4000年以后,大陆东南沿海陶器已经传至对岸的台湾岛[21];约公元前2500年以后,类似华南的圜底釜、豆等扩展到菲律宾一带[22];约公元前1500年后,圜底釜、豆等因素抵达美拉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西部地区[23]。这一陶器传播路线,大致也就是稻作农业传播路线,被认为与南岛语族的起源和扩散有关[24]。
4.向西 约公元前4000年之后,庙底沟式彩陶最西扩展至青海东部和四川西北部。约公元前3500年以后,甘青等地的马家窑文化西进河西走廊,西南踏上青藏高原,其影响余绪甚至一度抵达克什米尔地区。约公元前2500年以后,马家窑文化最终扩展至新疆东部。约公元前1500年以后,源于甘青的彩陶,从新疆东部西扩至天山南北大部地区,最远到达费尔干纳盆地甚至土库曼斯坦西南[25]。这些彩陶文化所至之处,大致也就是粟作农业到达之地。在哈萨克斯坦和克什米尔地区发现公元前2000多年的黍[26],很可能就是通过这一路线传播而去。
东方的玉器、漆器、丝织品等都是独具特色的器物。玉器最早出现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阿尔泰和外贝加尔地区,公元前5000多年后,从中国东北传到江浙、海岱等地[27],为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大汶口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等中国东部新石器时代文化增添了不少温润之气。公元前2500年后,东部玉器趋于衰落的同时,中原、江汉、陕北都有了较为发达的玉器,甚至一度向西传播到甘青地区。约公元前2000年以后,源于黄河中下游的玉牙璋甚至远距离扩散到东南亚地区[28]。漆器至少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的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等当中已经出现,良渚文化时期已很流行。丝织品的产生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五千纪,商周时期已经非常发达。至战国晚期,漆器和丝织品已经西传到新疆天山和俄罗斯阿尔泰地区[29]。
青铜器和铁器虽然都是西方起源,但传播到东亚以后,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大约公元前2500年以后,已经在中原地区形成复合陶范铸造青铜容器的独特传统[30]。公元前1600年以后,商式青铜器已经向北传到西辽河流域,向南至长江流域,向西达青海地区。铁器传入中国后,在约公元前8世纪,已经在中原地区形成独特的铸铁技术[31]。公元前5世纪以后,铸铁技术向东北传播到朝鲜半岛和日本[32],向西传播至新疆大部分地区[33]。
东方建筑形态多样,但最具特色的建筑技术有两项,一是榫卯结构的木构建筑技术,二是夯土技术。从公元前7000年前后中国东部各地出土的锛、凿等石器来看,当时在长江和黄河流域应当已经出现木材加工和榫卯技术,并且很可能主要用于房屋建筑。公元前5000年以后,榫卯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仅从石凿的分布来看,北达西辽河流域,南到东南亚,西至甘青地区,这应该也是榫卯技术所能辐射到的范围。夯土技术大约出现于公元前3000多年的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不但建房,而且筑城,就连土坯也用夯打模制技术,其影响向北至少到达西辽河流域。中国黄河中游地区在公元前7千纪就出现较大规模墓地,墓葬排列整齐,大致分区埋葬,以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占据绝对优势,每个墓地同时期墓葬在头向、墓室形制、葬式、随葬品等方面表现出大体一致的习俗。这种墓葬习俗后来扩大到上述陶器所确定的东方文化圈的大部地区。
总体来说,东方文化圈上述诸要素之间,互相有着密切联系,其根本在于定居和农业。东方陶器的出现早到2万年前,原初功能应当与对植物种子、鱼蚌等资源的烹煮食用有关,也应当是在一种较为稳定的攫取性经济条件下定居程度增加的体现。距今1万多年后,随着原初农业的诞生,定居程度进一步提高,陶器也越发丰富起来。最早出现的斧、锛、凿等磨制石器,主要为木工工具,应该与定居所需木构建筑的木料加工、榫卯结构制作等有关[34]。大约公元前4000年后,黄河、长江、辽河流域大部已经确立农业主体,形成“南稻北粟”二元农业体系,以及世界上最大的农业文化区。陶器复杂多样,彩陶盛行,漆器和丝织品开始常见,日常生活丰富,出现中心聚落,社会分化,形成早期中国文化圈。中国文化向四周的大规模拓展影响,大致也在这个时候。约公元前3000年,人群间冲突空前激烈,社会急剧复杂化,早期中国文明正式诞生[35],表意文字也应该在这个时候已经出现[36](尽管大量甲骨文、金文等的发现是在晚商以后)。另外,公元前3千纪末期出现的复合陶范青铜器铸造技术,公元前1千纪早期发明的铸铁技术,也都应当与中国悠久成熟的陶器烧造技术相关。
超大规模的定居社会和农业经济,长期以来潜移默化形成东亚地区稳定内敛、敬天法祖的观念,至少公元前6000年左右出现祭天仪式[37]、观象授时[38]和象数思维[39],以及排列整齐的多代“族葬”所体现的祖先崇拜、慎终追远和悠久的历史记忆传统,约公元前4000年后出现原初形态的礼制[40]。玉器虽然发源于西伯利亚地区,但在中国中东部最为发达,应该与玉所蕴含的温润、柔美、坚硬等内在特质相关,后来甚至演化为中国人的理想精神品质[41]。源自西方的青铜器技术,到中国则演变为铸造容器类礼器,成为物化社会秩序的中国特色器物。
二、早期西方文化圈
早期西方文化圈,核心在西亚,包括北非、中亚南部、南亚和欧洲南部地区。
广义西方最早的陶容器发现于北非,最早距今约12000年,但仅见碎片,与此后文化的发展关系不明。西亚地区最早的陶器,迟至约公元前6900年才出现,开始主要是一些素面的平底罐类器物[42],或为模仿之前该地区早已存在的石容器而来。西亚陶器出现不久,就开始流行彩陶,其发达程度超过同时期的中国彩陶,并向四周迅速扩展。西方农业和家畜饲养至少产生于约公元前9500年的黎凡特、土耳其至伊朗西北山地的“新月形”地带,主要种植小麦、大麦,养殖绵羊、山羊、黄牛等[43],之后即向四周传播[44]。公元前6900年之后,陶器、农作物和家畜以组合(包裹)的形式向四周的狩猎采集地区传播,多数情况下还伴随着人群的迁徙与交融[45]。
1.向北 源自安纳托利亚和黎凡特地区的线纹陶器,以及小麦、大麦等农作物,绵羊、黄牛等家畜,公元前5500年左右出现于欧洲中部,公元前5000年左右传播至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46]。
2.向西 陶器和小麦、大麦等农作物,公元前5500年左右已经抵达地中海东岸的法国、西班牙等地,公元前4000年左右抵达不列颠群岛[47]。
3.向南 黎凡特风格的陶器,小麦、大麦等农作物,以及绵羊等家畜,于公元前5000年左右扩散至包括尼罗河三角洲在内的北非地区[48];其后发展起来的埃及文明,向南影响到尼罗河上游地区。
4.向东 小麦、大麦等农作物,绵羊、黄牛等家畜,在约公元前6000年,东向-东南向到达中亚南部地区[49]。公元前3500年以后,绵羊、黄牛所代表的畜牧文化,可能包括小麦种植,通过亚欧草原已经向东扩展到新疆西部至叶尼塞河中游[50]。南线的农业、家畜等,公元前7000年以后逐渐扩展至印度河流域[51]。再向东,中亚式彩陶图案等传播至中国甘青地区[52],绵羊、黄牛、小麦等扩散至中国大部地区[53]。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约公元前3000年亚欧草原中部马的驯化,是受西亚绵羊和黄牛驯养技术影响的结果。约公元前3千纪末期在哈萨克斯坦西北部地区发明的轻型马拉双轮战车,源头也应当是西亚于公元前4千纪发明的黄牛、驴等牵引的实心轮车[54]。西亚式的实心轮车后传播至早期西方文化圈各处,最东到达中国的新疆地区,而马和马车则流播至亚欧大陆大部地区。
青铜器和铁器是早期西方文化圈影响深远的发明。这两种金属器除作为装饰品、容器、雕塑外,最主要的功能还是作为工具和武器,对于早期西方生产力的发展和对外大幅度拓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自然铜锻打的铜器在西亚最早出现于1万多年以前,人工冶铜在南欧和西亚至少始于公元前5千纪初[55],青铜器冶铸可早到公元前5千纪中叶[56]。铜器技术差不多和绵羊、黄牛、小麦一道,向四周扩散,约公元前3千纪已经传播到中国中原等地[57],公元前2千纪到达东南亚。陨铁的使用大约有5千年的历史,人工冶炼的铁器至少开始于公元前3千纪,公元前2千纪中叶已经传播到中国新疆和甘青地区[58]。
印章、雕塑、金器、釉砂等也是西方世界的典型文化因素。印章是具有凭证、象征意义的器物,于公元前7千纪已经出现于西亚[59],此后影响到埃及、伊朗、中亚、印度河流域等地;其与西亚楔形文字、埃及象形文字等的出现有密切联系,而楔形文字最后发展为表音的字母文字。人形和动物形雕塑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在西方世界流行,最早的陶质女人像(维纳斯)已有近3万年历史[60];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雕塑传统绵延不断,最具代表性者如埃及和希腊的雕塑,其影响则几乎及于早期西方文化圈大部区域。金器至少在距今1万多年以前就被西亚人认识和使用,其后这种阳光一样灿烂的金属深受西方人青睐,公元前5千纪的瓦尔纳(Varna)墓地就有大量金器随葬[61]。釉砂(费昂斯)在大约公元前3千纪左右出现于西亚,后在埃及发扬光大,并扩散至西方各地,公元前2千纪中期已经传播至新疆北部,公元前1千纪中叶已广见于中国黄河长江流域。此外,西方还很早就出现和流行香炉、香水、灯具等。有人还认为欧洲和中亚-中东分别是琥珀和青金石的主要分布区域[62]。
西方典型建筑以土石为特点,以土坯(日晒砖)、砖或石块垒砌墙体承重,就连柱子也常为石质,这在西亚、埃及、中亚都颇为流行。土坯(日晒砖)出现于距今1万年前的西亚,此后向四周扩展,向东于公元前3千纪末期已经传播到新疆东部和河西走廊。当然像欧洲平原地区,由于森林广布,自然多为木屋或者木骨泥墙房屋。早期西亚墓葬不见如裴李岗文化那样排列整齐的墓地,常见居室葬和天葬[63];后来在西亚、欧洲、伊朗、中亚等地还都常见火葬;直到公元前4000年前后,才在西亚、埃及、中亚等地开始较多出现族葬墓地。
早期西方文化圈的各要素之间互相也存在有机联系。西亚虽然也是最早的农业地区之一,但主要只是麦类农业体系,并未出现像中国那样两大农业体系并存的格局。西方能够发展农业的地方自然也不小,但农业中心区比较分散,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阿姆河流域由于彼此相隔较远,分别在公元前3千纪早中期形成相对独立的文明中心,而不像中国黄河、长江流域那样连成一片,形成体量庞大的多支一体的早期中国文明。西亚最早驯养的绵羊和黄牛,是需要较大草场牧放的家畜,从一开始就奠定了畜牧业的基础,其影响下在亚欧草原驯化的马更是典型的草原动物,使其文化从根本上具备了游动性更大、视野更广阔的特点,与中国依附于农业的家猪饲养不同。西方文明中心区之一就是地中海沿岸,交通多利用舟船和四轮车,后在亚欧草原又次生发明了双轮马车,其移动速度、距离,都非步行可比。
这些都使得西方文化具有相对更大的移动性和风险性。西方陶器不如中国发达,便于携带的金属器却更发达;西方居室葬和火葬更流行,神祇偶像崇拜优先于祖先崇拜,神祠、神庙繁多;西方青铜器和铁器发达,崇尚黄金、玻璃等具有耀眼光泽的器物,以及香炉、香水等挥发性强烈的物品,加上西方经济贸易发达,这也都会锻造出西方尚武、外向的文化特质。
三、早期北方文化圈
早期北方文化圈,主体就是亚欧草原,波及更北的森林-草原地带,以勒拿河和乌拉尔山为界,可将其分为东、中、西三部分,东南部延伸到中国东北、日本岛和朝鲜半岛,南部波及中国长城沿线,西南部至北高加索地区,西北部抵达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约公元前14500年以后,在日本、黑龙江流域和外贝加尔地区出现陶器[64]。其中,外贝加尔和黑龙江中游地区陶器多为尖底或圜底罐类,饰绳纹、篦纹等[65],和华南最早陶器近似,甚至口沿外饰一周珍珠纹的做法也更早见于玉蟾岩陶器,很可能是受到华南制陶技术影响的结果。日本最早的尖圜底素面陶罐、黑龙江流域下游最早的篦纹平底陶罐,虽和华南陶器差别稍大一些,但也不排除接受华南启示的可能性,当然具体器物形态或许与模仿或者借助当地编织物、树皮桶制陶有关。之后这类圜底罐就开始了难以置信的远距离扩展过程。向北于公元前4千纪抵达勒拿河中游[66];向西于公元前5000年后抵达芬兰,公元前4000年后最远抵达瑞典北部[67],被称作篦纹陶文化,先于西亚文化传统陶器抵达这些地区;西南向,于公元前6000年左右穿插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东部和河北张家口地区[68],于公元前5000年左右渗透进中亚阿姆河流域[69]。此外,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北部距今13000年以后的平底筒形罐[70],也当属于这个大文化圈,可看作是圜底罐的变异形式。就连中国太行山以东流行陶盂或直腹盆的磁山文化,实际上也和平底筒形罐甚至圜底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早期北方文化圈有着发达而绵长的细石器传统,最主要的经济方式是狩猎采集,其农作物和家畜主要源于其南的早期东方文化圈和早期西方文化圈,中国东北西辽河等地的黍、粟,虽然可早到公元前6千纪之初[71],但应当是从中国华北传播而来。亚欧草原西部里海和黑海北岸地区的小麦、绵羊、黄牛等,是从西亚地区传播而来。更为重要的是,如上所述,在西亚影响下,在亚欧草原驯化了马,次生发明了双轮马车,马和马车的出现及其向亚欧大陆各地的扩展,显示了亚欧草原的特殊地位和强大动力。
玉器是早期北方文化圈最重要的原创性文化因素,最早出现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阿尔泰和贝加尔湖地区[72],全新世之初传入中国黑龙江地区[73],公元前6000年左右南渐至西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公元前3500年以后盛行于红山文化和哈民忙哈文化。玉器的文化源头,应该就是最早产生于北非和亚欧大陆西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穿孔装饰品[74],当这类装饰品偶以西伯利亚玉石制作就成为玉器,并可能在使用过程中逐渐突出了其作为玉器的特性,实际上与水洞沟的鸵鸟蛋壳珠饰、山顶洞的骨石饰等,一开始并无本质区别。
雕塑传统也是这个文化圈的重要特征。中国东北地区红山文化素以“女神”像著称,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男性或者性征并不明显的人像,以及各种动物形象,往前还可追溯至公元前6000年以来兴隆洼文化、磁山文化、赵宝沟文化的石像、陶塑、人形“面具”等。西伯利亚草原中部的米努辛斯克盆地、阿尔泰至鄂毕河流域,公元前2000多年前后在奥库涅夫文化、切木尔切克文化等当中常见各种人形石雕或陶塑。中国东北地区的雕塑传统,或许有着东北亚旧石器时代的基础,红山文化的一些玉人和陶质“女神”像,就和贝加尔地区马耳他等遗址2万多年前的人物形象神似[75]。西伯利亚的雕塑传统年代很晚,传承关系不明,可能同时受到过来自早期西方文化圈和中国东北地区的影响。
作为早期北方文化圈主体的亚欧草原地带,实际上更是一个东西文化交流的快速通道。举凡西方发源的青铜器、铁器、金器、釉砂,以及小麦、绵羊、黄牛等,多半都是通过这个通道向东传播。而发源于中国华北的黍和粟等农作物,也顺此通道向西传播。而这些东、西方的典型要素,也成为早期北方文化圈的重要文化成分。
早期北方文化圈的狩猎采集和畜牧经济方式,决定了其定居程度不高,主要居住在简便易建的棚屋、帐篷等里面,但在南缘也有更为稳定的聚落和房屋,如8000年前张家口地区的半地穴式房屋,4000年前乌拉尔东南缘的圆形向心的多屋聚落等[76]。总体社会复杂程度有限,缺乏真正的文明中心。公元前1千纪前期图瓦地区的阿尔然游牧贵族大墓[77],代表了早期北方文化圈社会复杂化的最高水准,但缺乏相应的稳定聚落,更谈不上大型城市,难以论定这背后是否存在一个文明社会。该文化圈受东、西文化圈影响,墓葬情况东西有别,西部火葬成为一大特色。
总体而言,早期北方文化圈自具特色,含蓄内敛的玉器、宗教色彩浓厚的雕塑,都是萨满原始宗教的重要物质载体,萨满信仰所包含的万物有灵、三界联通等观念,也就成为早期北方文化圈的信仰核心,而萨满一般被认为与狩猎采集经济正相适应。当然,早期北方文化圈的确深受东、西两大文化圈的影响,从而使其东西有别。由于狩猎采集-畜牧经济的不稳定,文化延续性较差,人群游动性大,致使其不稳定性最高。
四、结语
全新世亚欧大陆三大文化圈的形成,深层背景在于自然地理环境。早期东方和西方文化圈的区分,关键在于青藏高原隆起造成的巨大障碍[78],从而分割出各自相对独立的两大地理单元和两大文化单元,使其人群长期主要在自己的文化圈内发展和交融。当然东、西两大地理单元的自然环境本身也有差别,存在西风带-地中海式气候和东亚季风气候的差别,以及地形地貌、动植物资源等的差别,从而为两大文化圈的各具特色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两大地理单元都属于中纬度地区,温度降水适中,土壤丰厚,所以都能发展出谷物农业,以及以其为基础的文明社会。早期北方文化圈则不一样,它和南部两个文化圈之间并无特别大的障碍,阴山、天山、高加索等一系列东西向山脉构成的大致的南北分界线,远不如帕米尔高原那样难以逾越。北方的相对独立,主要源于其高纬度、低温度,以及大体类似的草原-森林环境,整体更适合狩猎采集和畜牧经济。
三大文化圈虽然显著于全新世,但其实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就已现端倪,著名的“莫维斯线”就大致以帕米尔为界分出东、西两大石器技术传统[79]。其实在两大传统以北的亚欧草原西部地区,还有一个与前二者都有一定差别的传统。进入旧石器时代晚期,这三个传统的区别仍然大致存在。西方传统下,从旧石器时代早期精致规范的阿舍利手斧,到晚期的石叶技术、雕塑艺术、佩戴装饰艺术,早已体现出将人类意识强加于自然的精神,以及偶像崇拜的原始宗教观念。东方传统下,整个旧石器时代大体延续石片石器技术,罕见雕塑艺术,显示出质朴自然的风格。这些都与其后的西、东两大文化圈分别气韵相连。至于北方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有着发达的细石器工业,受早期西方文化圈影响而出现雕塑艺术、佩戴装饰艺术(包括玉器),形成萨满传统,传承到新石器时代,后期受东、西传统的影响较大,成为东、西交流的重要通道。
文化交流是三大文化圈发展演变的重要机制。早期北方文化圈和南部两大文化圈的交流,开始于全新世之初,开始主要是南部农作物和家畜的北传,约公元前2000年后,随着北方畜牧经济走向成熟,反过来对南方产生压迫,东、西长距离大范围的南北对峙局面在这时候初步形成。东、西两大文化圈的交流主要发生在公元前4千纪中期以后,彩陶、金属器、农作物、家畜等的交流,推动了东、西方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更进一步,日益增加的文化交流[80]使得三大文化圈之间的共性越来越多,终于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形成第二阶段的“欧亚世界”—如果说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全球化”造就了第一阶段“欧亚世界”的话。当然,文化交流并不总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三大文化圈之间存在较大范围的交互地带,这些地带是文化交流的结果,往往也是文化碰撞和人群冲突的前沿。
附记:2014年夏季在德国考古研究院做访问学者期间我有了“亚欧大陆三大文化圈”的构想,2015年春季在美国盖蒂研究所(Getty Research Institute)做客座学者期间以“亚欧大陆三大文化圈”为题和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的研究生们进行了交流。感谢德国考古研究院王睦(Mayke Wagner)教授和洛杉矶加州大学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等对我的帮助!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欧亚视野下的早期中国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编号18ZDA172)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向上滑动阅读正文
[ 1 ] a .Cohen K . M . , e t a l . ,International Chronostratigraphic Chart,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Stratigraphy, 2018.
b.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 Erster Band, Einleitender Theil, Berlin:Dietrich Reimer, pp.504-510, 1877.
[ 2 ] a.严文明:《长江文明的曙光—与梅原猛对谈录》,见《长江文明的曙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b.Colin Renfrew,Archaeology and Language:The Puzzle of Indo-European Origi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c.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见《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d.Peter Bellwood, The Checkered Prehistory of Rice Movement Southwards as a Domesticated Cereal-from the Yangzi to the Equator, Rice,4(3-4), pp.93-103,2011; Southeast Asian Islands: Archaeology, The Global Prehistory of Human Migration, Wiley-Blackwell, pp.284-292, 2015.
[ 3 ] a.E.N. Chernykh, Sarah Wright(Trans.), Ancient Metallurgy in the USSR: the Early Metal A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236,1992.
b.Hermann Parzinger, Die frühen Völker Eurasiens: Vom Neolithikum Bis Zum Mittelater,Verlag C. H. Beck, München, 2006.
[ 4 ] David Christian, Inner Eurasia as a Unit of World Histo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5, pp.173-211, 1994.
[ 5 ] a.叶舒宪:《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第20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b.李旻:《重返夏墟:社会记忆与经典的发生》,《考古学报》2017年第3期。
[ 6 ] a.P. L. Kohl, The Making of Bronze Age Eurasi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b.Barry Cunliffe, By Steppe, Desert, and Ocean:The Birth of Euras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
[ 7 ] a . P. L. Kohl , The Ancient Economy,Transferable Technologies and the Bronze Age World-system: A view from the Northeastern Frontier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Centre and Periphery in the Ancient Worl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13-24,1987.
b.Toby C. Wilkinson, et al.(Eds.), Interweaving Worlds: Systemic Interactions in Eurasia, 7th to 1st Millennia BC., Oxbow Books, 2011.
c.易华:《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中的中国》,见《全球史评论》第五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d.Nicole Boivin, Michael D. Frachetti(Eds.),Globalization in Prehistory: Contact, Exchange,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 8 ] 韩建业:《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 9 ] 吴小红:《中国南方早期陶器的年代以及新石器时代标志的问题》,见《考古学研究》(九)“庆祝严文明先生八十寿辰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2年。
b.Wu Xiaohong, et al., Early Pottery at 20,000 Years Ago in Xianrendong Cave, China, Science,336 (6089), pp. 1696-1700, 2012.
[10] a.张弛:《中国南方的早期陶器》,见《古代文明》第5卷,文物出版社,2006年。
b.陈宥成、曲彤丽:《中国早期陶器的起源及相关问题》,《考古》2017年第6期。
[11] Zhao Zhijun, The Middle Yangtze Region in China is One Place Where Rice was Domesticated: Phytolith Evidence from the Diaotonghuan Cave, Northern Jiangxi, Antiquity,278(72), pp.885-897, 1998.
[13] a.李有恒、韩德芬:《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动物群》,《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8年第4期。
b.凯斯·道伯涅等:《家猪起源研究的新视角》,《考古》2006年第11期。
c.罗运兵、张居中:《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出土猪骨的再研究》,《考古》2008年第1期。
[14] a.李水城:《中国北方地带的蛇纹器研究》,《文物》1992年第1期。
b.冯恩学:《俄国东西伯利亚与远东考古》第337~338页,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年。
[15] 张星德:《后冈期红山文化再考察》,《文物》2015年第5期。
[16]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农安县元宝沟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考古》1989年第12期。
[17] 赵宾福:《中朝邻境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比较研究》,见《边疆考古研究》第9辑,科学出版社,2010年。
[18] 冯恩学:《俄国东西伯利亚与远东考古》第204~211页,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年。
[19] a.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黑龙江肇源县小拉哈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8年第1期。
b.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肇源白金宝—嫩江下游一处青铜时代遗址的揭示》第30页,科学出版社,2009年。
[20] Zhao Zhijun, New Archaeobotanic Data for the Study of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in China,Current Anthropology, 52(4), pp.295-306, 2011.
[21] a.福建省博物馆:《福建平潭壳坵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第7期。
b.福建博物院:《闽侯昙石山遗址第八次发掘报告》第7~13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
[22] Peter Bellwood, Eusebio Dizon, The Batanes Archaeological Project and the “Out of Taiwan” Hypothesis for Austronesian Dispersal, Journal of Austronesian Studies, 1(1), pp.1-33, 2005.
[23] a.Peter Bellwood, Prehistory of the IndoMalaysian Archipelago, University of Hawai'iPress, 1997.
b.焦天龙、范春雪:《福建与南岛语族》第16~28页,中华书局,2010年。
[24]a.Peter Bellwood, New Perspectives on IndoMalaysian Prehistory, Bulletin of the IndoPacific Prehistory Association, 4, pp.71-83,1983.
b.张光直:《中国东南海岸考古与南岛语族起源问题》,见《南方民族考古》第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
[25] a.Han Jianye,“The Painted Pottery Road” and Early Sino-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s,ANABSASIS-Studia Classica et Orientalia, 3,pp.25-42, 2012.
b.韩建业:《再论丝绸之路前的彩陶之路》,《文博学刊》2018年第1期。
[26] a. Michael Spate, et al., New Evidence for Early
4th Millennium BP Agriculture in the Western Himalayas: QasimBagh, Kashmir,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Reports, 11, pp.568-577, 2017.
b.Spengler R.N., et al., The Breadth of Dietary Economy in Bronze Age Central Asia: Case Study from Adji Kui 1 in the Murghab Region of Turkmenistan,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Reports, 22, pp.372-381, 2018.
[27] 邓聪:《东亚玦饰四题》,《文物》2000年第2期。

[28]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编:《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庆祝郑德坤教授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周年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
[29] a.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阿拉沟竖穴木椁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期。
b.Sergei I. Rudenko, M.W. Thompson (Trans.),Frozen Tombs of Siberia: The Pazyryk Burials of Iron-Age Horseme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3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首次发现铜器》,《考古》1984年第12期。
[31] 韩汝玢:《天马-曲村遗址出土铁器的鉴定》,见《天马-曲村(1980-1989)》第1178~1180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
[32] a.王巍:《东亚地区古代铁器及冶铁术的传播与交流》第146~16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b.白云翔:《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第366~372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
[33] 韩建业:《新疆地区的早期铁器和早期铁器时代》,《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7期。
[34] 钱耀鹏:《略论磨制石器的起源及其基本类型》,《考古》2004年第12期。
[35] 严文明:《略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1992年第1期。
[36] 王晖:《中国文字起源时代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37] 湖南洪江高庙遗址的“排架式梯状建筑”,与白陶上的“天梯”图案互相对应,加上兽面纹、鸟纹等与“天”有关的图案,以及可能为燎祭后瘗埋的动物牲坑、人牲坑等,足以复原出一个可信的通天祭祀场景。参考如下文献。
a.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黔阳高庙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4期;《湖南洪江市高庙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06年第7期。
b.贺刚:《湘西史前遗存与中国古史传说》第254~262页,岳麓书社,2013年。
[38] a.贺刚:《湘西史前遗存与中国古史传说》第
330~344页,岳麓书社,2013年。
b.冯时:《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与制度》第46~7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
[39] 宋会群、张居中:《龟象与数卜:从贾湖遗址的“龟腹石子”论象数思维的源流》,见《大易集述:第三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巴蜀书社,1998年。
[40] 韩建业:《西坡墓葬与“中原模式”》,见《仰韶和她的时代—纪念仰韶文化发现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
[41] 费孝通:《中国古代玉器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思想战线》2003年第6期。
[42] a.Chris Scarre, The Human Past: World Prehisto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ies (Third Edition), Thames & Hudson,pp.231-233, 2013.
b.杨建华:《两河流域:从农业村落走向城邦国家》第56~63页,科学出版社,2014年。
[43] a.Bar-Yosef, Ofer, Richard H. Meadow,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in the Near East, Last Hunters, First Farmer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Prehistoric Transition to Agriculture,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pp.39-94,
1995.
b.Melinda A. Zeder,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in the Near East, Current Anthropology, 52(S4),pp.221-235, 2011.
[44] Colin Renfrew, Archaeology and Language: The Puzzle of Indo-European Origi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46] T. Douglas Price, Ancient Scandinavia: An Archaeological History from the First Humans to the Viking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47] Nicki J. Whitehous., et al., Neolithic Agriculture on the European Western Frontier: the Boom and Bust of Early Farming in Ireland,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51, pp.181-205, 2014.
[48] D. W. Phillipson, African Archaeolog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49] A. H. Dani, V. M. Masson(Eds.),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Volume I: The Dawn of Civilization: Earliest Times to 700 B.C., UNESCO Publishing, 1992.
[50] a.Hermann Parzinger, Die frühen Völker Eurasiens: Vom Neolithikum bis zum Mittelater,Verlag C. H. Beck, München, pp. 169-243, 2006.

b.李水城:《从新疆阿依托汗一号墓地的发现谈阿凡纳谢沃文化》,《新疆文物》2018年第1、2期。
[51] Jarrige C., et al.(Eds.), Mehrgarh: Field Reports 1974-1985, From Neolithic Times to the Indus Civilization, Karachi: The Depart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Government of Sind,Pakistan,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French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1995.
[52] 同[25]b。
[53] a.傅罗文等:《论中国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家养动物的来源及特征》,《考古》2009年第5期。
b.董广辉等:《农作物传播视角下的欧亚大陆史前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科学:地球科学》2017年第5期。
c.Tengwen Long, et al., The Early History of Wheat in China from 14C Dating and Bayesian Chronological Modelling, Nature Plants, 4,pp.272-279, 2018.
[54] a.Kuzmina E. E., The Prehistory of the Silk Road,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7.
b.David W. Anthony, The Horse, the Wheel and Language, Princeton &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55] D. Šljivar, The Earliest Copper Metallurgy in the Balkans, Metalurgija-Sisak then Zagreb,12(2), pp.93-104, 2006.
[56] Thornton C., et al., On Pins and Needles: Tracing the Evolution of Copper-base Alloying at Tepe Yahya, Iran, via ICP-MS Analysis of Commonplace Item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29 (12), pp.1451-1460, 2002.
[57] 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
[58] a.陈建立等:《甘肃临潭磨沟寺洼文化墓葬出土铁器与中国冶铁技术起源》,《文物》2012年第8期。
b.同[33]。
[59] 马欢欢、杨建华:《西亚史前印章记录系统的发展和演变》,《考古》2018年第6期。
[60] Conard Nicholas J., A Female Figurine from the Basal Aurignacian of Hohle Fels Cave in Southwestern Germany, Nature, 459(7244),pp.248-252,2009.
[62] David A. Warburton, What might the Bronze Age World-System Look Like? Interweaving Worlds: Systemic Interactions in Eurasia, 7th to 1st Millennia BC., Oxbow Books, pp.120-134,2011.
[63] a.J. Mellaart, Catal Hüyük: A Neolithic Town in Anatolia, New York: McGraw-Hill, pp.204-209, 1967.
b.J. Mellaart(Ed), Excavations at Hacilar,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70.
c.F. el-Wailly,B. Abu es-Soof, The Excavations at Tell Es-Sawwan: First Preliminary Report(1964),Sumer, 21, pp.17-32, 1965.
[64] a.Cohen D. J., The Advent and Spread of Early Pottery in East Asia: New Dates and New Considerations for the World's Earliest Ceramic Vessels, Journal of Austronesian Studies, 4(2),pp.55-90, 2013.
b.Yaroslav V. Kuzmin, Chronology of the Earliest Pottery in East Asia: Progress and Pitfalls, Antiquity, 80(308), pp.362-371, 2006.
[65] Yanshina O. V., The Earliest Pottery of the Eastern Part of Asia: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441(Part B), pp. 69-80, 2017.
[66] Мочанов Ю.А., Многослойная стоянка Белькачи I и периодизация каменного века Якутии,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69.
[67] Ove Halén, Sedentariness During the Stone Age of Northern Sweden: in the Light of the Alträsket Site, c. 5000 B.C., and the Comb Ware Site, Lillberget, c. 3900 B.C.: Source Critical Problems of Representativity in Archaeology, Acta Archaeologica Lundensia: Series in 40 No.20, Almqvist & Wiksell International, 1994.
[68] a.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内蒙古化德县裕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21年第1期。
b.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北尚义县四台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8年第4期。
[69] 捷尔特米纳尔文化(Kelteminar)。参见
A. H. Dani, V. M. Masson(Ed.),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ume I: The Dawn of Civilization: Earliest Times to 700 B.C.,UNESCO Publishing, 1992.
[70] a.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安市后套木嘎遗址AⅢ区发掘简报》,《考古》2016年第9期。
b.王立新:《后套木嘎新石器时代遗存及相关问题研究》,《考古学报》2018年第2期。
[71] 同[20]。
[72] a.Герасимов М. М., Палеолитическая cтоянка Мальта (pаскопки 1956-57 годов),Советская этнография, № 3, 1958.
b.Okladnikov A. P., Paleoliticheskiye Zhenskiye Statuetki Bureti (Paleolithic Female Statuettes from Buret), Paleolit i neolit SSSR, 4, MIA 79,pp.280-288, 1960.
[73] a.佳木斯市文物管理站、饶河县文物管理所:《黑龙江饶河县小南山新石器时代墓葬》,《考古》1996年第2期。
b.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饶河县文物管理
所:《黑龙江饶河县小南山遗址2015年Ⅲ区发掘简报》,《考古》2019年第8期。
[74] 魏屹等:《旧石器时代装饰品研究:现状与意义》,《人类学学报》2016年第1期。
[75] Anatoliy P. Derev’anko, et al. (Eds.), Inna P. Laricheva(Trans.) , The Paleolithic of Siberia: New Discoveries and Interpretation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Urbana and Chicago, pp.122-128, 1998.
[76] 以辛塔什塔(Синташта)聚落为代表。参见Генинг В. Ф., Зданович Г. Б., Генинг В. В.,Синташта: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памятник арийских племен Урало-Казахстанских степей, Ч. 1, Челябинск, 1992.
[77] a.Michail Petrovič Grjaznov,Der Großkurgan von Aržan in Tuva, Südsibirien, München: Verlag C.H.Beck, 1984.
b.Konsgtantin V.Čugunov, Hermann Parzinger, und Anatoli Nagler, Der Skythenzeitliche Fürstenkurgan Aržan2 in Tuva, Archăologie in Eurasien Band 26, Steppenvölker Eurasiens Band 3, Verlag Philipp Von Zabern·Mainz,2010.
[78] 王幼平:《青藏高原隆起与东亚旧石器文化的发展》,《人类学学报》2003年第3期。
[79] a.Movius H. L., Early Man and Pleistocene Stratigraphy in Southern and Eastern Asia,Papers of the Peabody Museum of American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Harvard University,19(3), 1944.
b.Stephen J. Lycett,Christopher J. Bae, The Movius Line Controversy: the State of the Debate,World Archaeology, 42(4), pp.521-544, 2010.
[80] Peter Bellwood,The Global Prehistory of Human Migration, Wiley-Blackwell, 2015.
(作者:韩建业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原文刊于《考古》2021年第11期)
责编:韩翰
- 随机文章
- 热门文章
- 热评文章
- 2021年养殖业什么最赚钱农村 2021年农村养殖什么赚钱最快
- 一刻钟等于多少分钟 古时候一刻钟等于多少分钟
- 苹果树种植 苹果树种植时间
- 蜜蜂养殖教程大全 蜜蜂养殖教程大全图片
- 柞蚕每次眠多久几天一眠
- 清汤鱼火锅的做法 清汤鱼火锅的做法 家庭窍门
- 农村养肉狗赚钱吗 在农村老家养肉狗赚钱吗
- 海水稻 海水稻的生殖方式